

【大靖明月】微信平台2018年第016期
编者按:
这篇无名作者的文字,写出了几代山区求学人的记忆几代人的泪。强烈推荐。
老侯人实在,就如请来的山里厨子。左一盘肉,右一盘肉,直把个磨石沟村端地是肉香腾腾。老侯站在边上,一个劲谦让满桌的宾朋,“吃,吃,往饱里吃,咱山里再没啥可吃的、就是个肉么。”自己连筷子都来不及动一下。可他笑得比谁都生动,没办法,儿子娶媳妇,由不得。
“就是个肉么。”车过团庄学校,又想起老侯的那一句话来,觉得有时候生活也真够幽默的。
曾几何日时,盯着碗里零星的几朵油花,把饭缸子翻了一遍又一遍,愣是没找出所谓肉饭里的一丁点肉来。把肉和做肉的人骂了千遍万遍。以梦为马,莫负韶华,站在清冷的傍晚,狠狠立了人生第一个志向:肉,等着!总会有个彻底了断的。

三十年前,村级初中坼迁合并,大批学生一下子涌进乡镇中学,让毫无准备的学校一时无所适从,就像一对忽然接受孩子出生的小夫妻,首尾难顾,漏洞百出。期间,我也成为了浩浩荡荡求学队伍中的一员,背着铺盖卷,翻越千山万水,来到人生的第一个驿站——团庄中学。老师居然有女的,居然说一口流利的听不懂的语言。山里孩子的世界被猛然打开,满眼都是惊奇和新鲜。新鲜的还有白杨椽子扎成的木床,歌曲“小小竹排江中流”中的那种。只可惜作木筏可以,作床真是勉为其难了,单簿的褥子搭上去,只可眼观,不可实用,身子搁上去,一晚上硌得浑身生疼。有亲朋好友的送些草垫,蛮不错,苦了我们这些举目无亲的孩子。有一年,去的晚了,只剩椽头处巴掌宽一绺,严重畸形的椽梢在背部高高突兀,又在臀部深深下陷,睡上去几乎保持着半起立的姿势,当年鬼子折磨地下党贯用的那种刑式。再看平展的椽根部位,羡慕的要死,幸福近在咫尺。
上一级的老乡却不以为然,说你们已经很不错了,我们那阵哪有床呀,全是地铺,顺着墙根垫些麦草,一圈儿席地而卧,由于是教室改造的,潮湿的历害。没几天,好多人浑身出疹子,蛮吓人的,一学期没完,都溜得差不多了。想想他们的遭遇,觉得自己够幸运了,急忙咽回去一肚子怨屈,幸福感陡然猛增:人呀,还是得知足。

团庄三年,最不能忘记的是饮食。一日三餐,早晨、中午馒头,都是由自已从家背的。十几里山路不拒绝脚步,弓背弯腰走在漫长的山间小路上,走了朝晖走夕阳,走了盛夏走寒冬,直到把懵懂少年走成了多愁善感的青年。个子没长高,一直觉得跟那段岁月不无关系——挣掉了。最重要的还是营养,几口开水,一口干馍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哪能补足?馍,还不能随心所欲吃饱,背的少,得有计划,满打满算一周。青春敏感期,挺有自尊,觉得一个无所事事的劳力,吃闲饭,挺难为情,那是个读书可有可无的年代,读书人并非吃香,于是悄悄将母亲加进去的馒头取出来,用饥饿的折磨来弥补隐隐的歉意。
路过石窑子,南墙根谝谎的闲人齐刷刷将目光投过来,一阵无所适从。有人故意取笑,高声打趣说:“又是一帮送饭的、不回家娶媳妇去。还念哪门子的书呀?大晃晃的!”更加无地自容了。
山里孩子读书晚,要经历爬山背馍的苦楚,要留级到能承受这般生活压力时方可去外地求学,所以块头都比较大,人家如此调侃也有道理。但恰恰戳到我们软肋了,加快脚步,逃也似走过,一路上,大家再没出声。
夏天还不错,无论是泡还是怎样,馒头都能被轻松摄入。最怕的是冬天,地冻天寒,馒头成了个冰疙瘩。咬,咬不动;掰,掰不开。顺着边缘慢慢唆,化一点,唆一点,等唆完了,嘴唇冻得没了知觉。有人想个法子,在底部挖个小坑,倒进开水融化,然后用勺子掏,化一阵掏一阵,掏一阵,化一阵,速度大有长进。

与馒头冻得一样冰冷的还有我们。教室改制的宿舍空间偌大,冷风积满一屋子,与屋外的温度并无二致。外面结冰,里面照样冰花满屋,破损的窗户寒风呼呼,露出被子外的两只耳朵都没了知觉。也有人想出法子,傍晚在河滩读书时找来光滑干净的石头,在教室的铁炉上烘烤,晚自习一下,抱了暖暖的石头往宿舍跑,一进宿舍,立刻与暖石和衣而睡,只有如此,才能睡倒冻僵的身体。后来,效仿的人一多,争争抢抢中,反而谁都做不成了。
还是要说说饮食,尤其学校提供的那一顿,因为年轻,身体对食物的向往才是刻骨铭心的。
无论多少年过去了,只要鼻孔里捎进哪怕一丁点儿那种熟悉的味道,神经立刻会敏感起来。若是夜里,会身不由已置于奔跑抢食的境地。那是一种黏黏 的、苍白而毫无内容的气息,将生面倒进开水里煮,而后平白无故放进一些菜叶,升腾的雾气中便会散发出那种激发人好奇欲望的气味,是饭吗?会是一种怎样的饭食呢?但它确实是饭,并且是供给几百人食用的汤饭。一个胖胖的男人叉腿骑在锅沿上,用一把铁锨使劲搅拌,朦胧的雾气氤氲了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,长长的队伍不敢有丝毫造次,因为稍有不敬,他会将盛满汤饭的勺子在空中毫不犹豫拐一个弯,径直奔向别人的饭缸,留下发懵的你在那里独独地尴尬而惊慌。

若是夏天,汤面上总会漂浮一些不知好歹的飞虫,用筷头一下一下地蘸,起初,尚能蘸尽,到后来是越蘸越蘸多,只好躲到光线昏暗处,眼不见心不烦。最怕那些浮肿发白的小菜虫了,一筷子撬起,纤毫毕现,能让人喉咙里发毛好几天。
要说说肉了,虽然那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形式,但它承载着的无数希望却如满天星辰一样照亮了许多个黑夜。
每学期只一次肉饭,很像凉州的羊肉香头子,气味很强,诱惑很大,满校园都是肉香飘飘。和老侯蹲在离灶房不远的一处阴凉里,吃得是满脸大汗。吃了好半天,始终没见着一点肉丁,就亳不甘心地说:“唉,肉呢?怎么一点都没有?”老侯咂着嘴一脸愤怒,说:“吃吧!能有肉?早让灶大师那些孙们吃完了,还能轮上我们?你不看他们那一个一个肥猪的一样。”大家就觉得灶大师的那付身板确实不地道。

老侯让我看好饭缸,自己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另一个空缸子,欠起身体作好了快跑的准备。因为每次肉饭都觉得吃不饱,吃不尽心,弥补缺憾的唯一办法就是加饭。偌大一个饭锅,每次剩点也在所难免,师傅们又不是神仙。可加饭的又何止一二,尤其肉饭,稍一慢怠,连锅前都挤不过去。所以,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:一是别离灶房太远;二是让老侯亲自上马,他有速度优势。
万事俱全,只欠东风,只听师傅在灶房口大喊一声:“加饭了(liao)!”老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离弦而去,将其他娃娃们远远甩在了身后。后来,看过刘翔在奥运会的百米冲刺,我都有些不以为然。
有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搭伴读书,真好!
傍晚读书归来,路过教师灶房,洞开的窗口雾气升腾。老侯说包子呀!我说你咋知道?他说晚饭时看见师傅们在包,那肯定是包子无疑了。走出好远了,老侯转过身又看了看。
“要不取两个?”他心有不甘,很有分度地将“偷”说成了“取”。看我顾虑重重,鼓劲说:“没事,你放哨,我上!”
他刚钻进窗洞,斜对面师傅的房门开了。一束光线打过来,正好照亮了老侯即将消失的身影,“谁?”一声断喝,我撒腿便跑,身后传来了一声心惊肉跳的闷响。
好一阵,老侯才一瘸一拐地走过来,帽子和脸上都沾满了土。看见我,一脸惊喜,拳头一伸说:“给!包子,是肉馅的!”
作者姓名详,见到后,请与平台联系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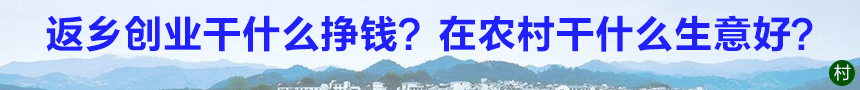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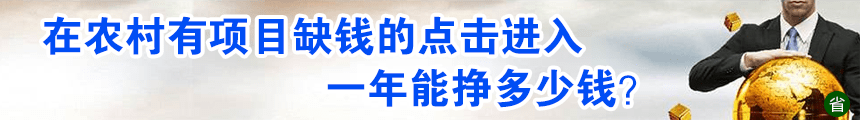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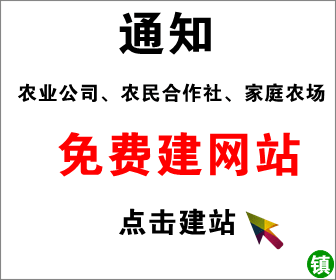
 苏ICP备18063654号-3
苏ICP备18063654号-3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
